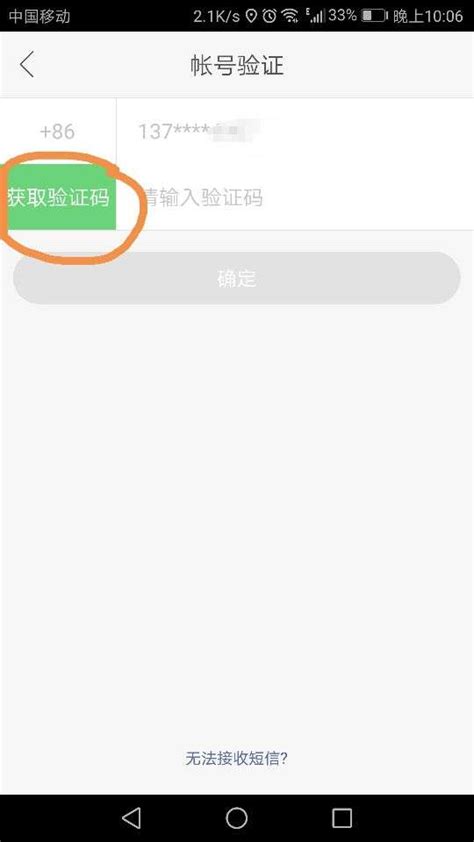作者:詹丹
2021年9月4日,我坐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演出大厅,从下午连晚上,第一次观看了喻荣军编剧、曹艳导演的《红楼梦》全本话剧,这也是全本话剧的首场演出。2022年9月4日,我坐在上海大剧院,第二次观看话剧《红楼梦》。至此,在整整一年时间里,话剧《红楼梦》在上海转换三个场地,又在杭州、深圳等地巡回演出,已经全本演出了21场。
首场演出前,我和编剧喻荣军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有过一次对话,首轮演出结束后,我又和导演曹艳对话了一次。两次对话,让我深切感受到编导另一种意义的对话意识,就是他们站在现代、站在当下而与古典名著展开的强烈对话意识。
在以往的戏剧或者影视剧改编中,不少编导都会把忠实于原典作为自己改编创作的宗旨,比如赵清阁继多次改编《红楼梦》为话剧后,又在1950年代改编成话剧《贾宝玉与林黛玉》,就是在其“自序”中这么自我期许的(“把这部伟大古典巨著忠实地再现于舞台”)。1987版的电视剧《红楼梦》,乃至2010版的电视剧《红楼梦》的编导都宣扬过这样的立场,而且有的也得到了观众很大程度认同,如对87版电视剧。但这种忠实的改编和再创作在多大程度上扣紧了作者原作的思想艺术,还是有不少讨论余地。因为当作品的文字需要活生生的人物来演绎,并附之以各种声光效果时,即使我们把忠实定位在原著的精神气质层面,但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性,已经让真正的忠实或多或少变成了改编者主观上的一厢情愿,或者说是客观上无法超越的地平线。这样,干脆放开手脚,明确自身的现代人立场,借改编与古典名著展开对话,反而为自己的创作打开了大有可为的天地,这是喻荣军和曹艳合作编导话剧《红楼梦》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以下省称“新编话剧”)。此前的越剧《红楼梦》,在删繁就简、大加删削方面,就作出了成功的探索。
新编话剧《红楼梦》剧照
这种对话,当然没有采用在舞台中设计出一些编剧和导演观念的代言人,来直接上场与人物对白,或者向观众独白(尽管有些编导也这么尝试过),而更多内化为整体情节设计的结构张力,内化为剧中人物的心灵独白、旁白,以及人与人之间具有结构意味的对话。
在原著中,大荒山下动了凡心的通灵宝玉与情种贾宝玉,构成切入小说的家族史和情感史的两个基本视点。随着情节的展开,当通灵宝玉的功能渐趋淡化时,理家的王熙凤,把展现家族史的通灵宝玉的那个特定视点取而代之了,形成凤姐对应于家族、宝玉对应于情感的两条结构线索。此外,携带通灵宝玉入世的一僧一道以及只在人物梦中出现的警幻仙姑则始终保持着出世的超迈性,是入世中两个视点而外的“第三只眼”。但在新编话剧中,对整体视点作了大刀阔斧的改变。出世的视点一概以警幻仙姑来统摄,同时,在入世的视点中,家族的视点,分裂为贾政和凤姐两个立场,前者强调礼仪的压力、社会角色的压力乃至做人的压力,以他的跪拜为象征符号,开启话剧序幕,形成情节转折的关键点之一;而凤姐,则是以她的梦幻般的视点,审视了家族成员受自然欲望驱动而带来的乱象,贾珍的乱伦、贾琏的淫荡、贾瑞的色迷心窍等,如梦魇般围绕凤姐展开。相对来说,贾宝玉周旋于女孩中的那个视点,脂砚斋批语所谓,“通部情案,皆必从石兄挂号”的特点,没有太大变化。
贾政功能的提升和凤姐的重新定位,其实都应该在新编话剧强化了的警幻仙姑的功能中得到结构化理解。在贾政、凤姐等把入世的压力全部内化为心灵感受,一种似乎无法承受之重时,那种出世的飘逸、轻盈感,在警幻仙姑默默穿梭于舞台中,获得了大开大合的张力,这是重与轻的对话,也是言说与沉默的对话。这种内在于结构的对话,促使观众从现代人角度思考了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
如果这样的整体结构意义的对话略显形而上的话,那么,一些情感纠葛的细节处理,让现代意识渗透进古典作品,让现代与传统构建的对话,如同人体解剖是猴子解剖的一把钥匙那样,以现代更为成熟、发展了的思想情感来照亮古典的隐晦萌芽,也是完成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贵尝试。这里举两个例子。
其一,小说第二十三回写宝黛共读“西厢”,宝玉以《西厢记》中张生的“多愁多病身”和莺莺的“倾国倾城貌”台词来类比自己和黛玉的关系,开玩笑式的表白自己、试探黛玉,结果引得黛玉当场发怒,指责宝玉是用混话来欺负她。但在新编话剧中,当黛玉听闻宝玉这番“戏语”,先有一段害羞、回味的时间,甚至自己还接口念叨起来,经过自身情感的波澜和延宕,才突然一变为动怒的情绪,才开始指责起宝玉。也就是说,原著中人与人的外部冲突在话剧中内化为人物自身的心理感受,才使得这种冲突更具立体性,也为现代主体意识延伸至古典作品,提供了可能。
其二,柳湘莲与尤三姐订婚而又反悔,导致尤三姐在柳湘莲面前自刎。这一幕,小说是在瞬间完成的,尤三姐一句“还你的定礼”刚出口,已让自己命陨当下。在这过程中,并无谈及自己和湘莲的情感,也没有再给湘莲以说话的机会。不过,小说也写了尤三姐亡后幽灵与湘莲见面,既有对自己苦守多年的告白,也有对湘莲“冷心冷面”的指责。这种处理,对具有现代意识的观众来说,并不适宜。所以当初赵清阁在改编的话剧中,设计了尤三姐临终前的一段对白:柳湘莲对尤三姐表白情意,而尤三姐回答说“太晚了”来归结他们的情缘,强化了人物无法挣脱传统观念而造成的巨大遗憾。在新编话剧中,则是让拔出剑来的尤三姐,与柳湘莲有一段双人剑舞,把不了的情意,在舞姿中表达得凄艳、含蓄而又无奈。这样的处理,是能够让观众有相当的共情体验的。
当然,把现代意识具体化为艺术手段,与传统经典在舞台上建立对话关系,需要以保持差异性为前提,没有差异的对话是无从谈起的。那么,如何不让彰显的现代意识遮蔽传统观念,而只是让两种意识发生充分撞击,让观众更清晰认识到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质,新编话剧中的有些细节处理还需要再斟酌。比如抄检大观园一场戏中,晴雯被王夫人逐走,新编话剧是让两个壮汉把晴雯架出去,这对表现晴雯的无力感当然很生动,但须知,按当时礼仪,一则王夫人不可能让壮汉做她的跟班,二则大观园作为清净女儿世界也不是那些壮汉可以进入的。所以要逐晴雯,也只能让身边的老婆子仆妇们作帮凶来下手,这也正是贾宝玉会骂老婆子是鱼眼睛的缘故之一。但新编话剧就这么“粗暴”处理了,这是对晴雯的粗暴,也是对《红楼梦》的粗暴了。类似欠妥的细节处理还有一些,说明新编话剧在一年来的演出中取得初步成功后,还需要在局部上进一步细细打磨,在演出方面也还有着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我相信,继越剧《红楼梦》、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外,新编话剧《红楼梦》可以成为又一部经典改编之作。从已有的基础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着。
(作者詹丹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红楼梦与江南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STA006)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内容由用户自行上传,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处理,谢谢!联系QQ:276037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