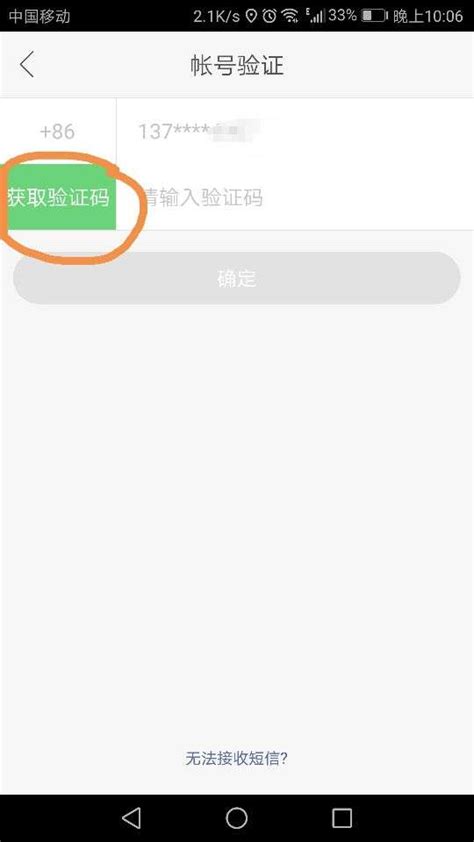信推送排序规则改变,第一时间看淳学文章需右下点赞和在看建立深度阅读关系
古今往事一壶茶,浪奔浪流上海滩!
我是周子淳,在沪29年,以淳报视角,播报真实上海!
本期播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亡命天涯,远走海外的上海人
2001年,在黄河路结束了一个商务宴请,顶头上司江经理突然有了兴致,说:小周,我们去外滩白相,11路公交车(到外滩逛逛,走路去)。
我们的公司在徐家汇,江经理住在虹口区,每天骑摩托车上班抱着头盔,进门,打卡。
这是已经过了晚上9点,黄浦江的风吹来,非常舒服;人也不多。有一些轮船在江上来来往往。
我看了一下南边的十六铺码头,有点感慨:江经理,95年我来上海时,就是在十六铺码头下船的。
江经理笑了:哈哈,大部分的老上海人,和你一样,也是在在十六铺码头下船的。
他进一步解释:上海本来就是移民城市,早年的上海人,江浙皖居多,尤其是宁波人和苏北人;之后豫赣鲁,以及全国的人都来;全球的时局很乱,aguolin(外国人)也来,例如英法美日,犹太人,白俄等,毕竟是远东第一城市。
小周,你现在见到的上海人,极少有四代及以上的。
以前水路发达,船票便宜,旅途时间虽长但那时候的时间不值钱。走京杭运河,走长江,海上经过长江口进入黄浦江;周边的湖州、周庄、南浔等,都有码头,四通八达。
反而陆路来上海,七绕八弯,哪怕是从上海到苏州的往返都不算方便。
我问:江经理,据说十六铺码头是杜月笙的发迹之地?
江经理:对的,杜月笙鬼精鬼精的,看势头不对,在1949年4月全家迁往香港,带上了孟小冬。
我问:那个年代,外逃的人多吗?
江经理:当然多!旧上海鱼龙混杂,达官贵人也很多。看国民党的形势不对,在杜月笙跑路之前,已经走了一大波人。杜老板家大业大,很多人跟着他吃饭。他也是观望了一阵子,我党也做过工作,但他还是担心“血债血偿”,不愿留下来;他对国民党也失望,不肯去台湾;最终选择了香港,他认为这样可以进退自如。
杜老板也劝过黄金荣,但黄年纪大了,过了80岁,因而不肯走。
黄金荣被劳动改造,1953年过世。有些人看到黄金荣拿着扫帚扫大街,于是在50年代,“机灵”的人就纷纷走了。
我问:哪些人会走?
江经理:这就非常非常复杂了。主要有以下三类:
1、以前跟国民政府走得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人很清楚,吃香的,喝辣的时代结束了;
2、觉得时局不明,正好有海外关系,可以去投靠的;
3、在建国初期,对三反五反等多个政治运动很不适应,不感冒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单位或者自己居住的弄堂不受待见。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大多数人是没有选择的,只好随波逐流顺水推舟;然而能留在上海的,都是一些有门道有本事的人,他们知道一个道理: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机会,就逃了!
我问:这些人走得了吗?
江经理笑了:那时的上海,并不是孤岛,也并不是你想象的戒严封闭,政治清算!相反,作为远东的大城市,内部氛围是积极热烈的,新中国建立后,所有人都憧憬未来,投入到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加上苏联的援助,很多工业项目拔地而起,全国人民充满热情和干劲;作为外部来说,与海外的交流非常频繁,新中国百废待兴,很多物资都缺,需要外部运来,人货物交流频繁。
因而,因公派遣,留学,投奔海外亲友,理由是非常多的;当然,这些都需要手续齐全,遵守政策。
我问:他们会到哪里去?
江经理:首选当然是香港,美英及国民党当局,和苏联及我国大陆政权敌对,但香港是当时各方都能接受的中转站。
到了香港后,少部分会定居香港,例如汪明荃,1947 年 8 月 28 日出生于上海崇明岛,9 岁时移居香港。
很多人会辗转去美国,毕竟美国是第一强国。
去欧洲的也有,我的一个远房叔叔,50年代初,他还在襁褓中,家里人接到一封海外来信;他的父母是工厂技术骨干,走不了,于是把他托付给家里的老保姆,先去香港,然后去了德国。
去日本,或者去对岸,也很多。
我问:他们怎么走?
江经理: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和香港之间有固定的海上航线;飞机也有,国泰航空和中国航空经手的;之后多年,两地始终有持续性的交通往来。
当时有“桥上过”和“桥下过”的说法,前者属于正规途径,手续齐全,申请审批不易。我爸有个小学同学,姓曹,住在高安路少年宫对面的那个铁门后面,家里有点来头,后来办理了手续去了香港。八十年代,曹叔叔来我家吃饭,粤语很溜了。
“桥下过”就是偷渡了,九死一生。小周,你不是看过《卫斯理》的小说吗?作者倪匡是1957年去的香港。
1951年,他父母带着家中三个孩子先去了香港。16岁的倪匡,初中毕业后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受训。结业后,他前往内蒙古垦荒。在内蒙古时,倪匡因拆毁木桥当柴烧等事,被怀疑为“反革命”而接受隔离调查。为躲避调查,1957年,他伪造多种公章、证件、介绍信由内蒙古畏罪潜逃至广州,七月间偷渡至澳门,最终逃到香港。
那个年代,海员很吃香,尤其是远洋轮船。
王家卫5岁时去香港,他的父亲就是海员。
江经理喝了一口水,说:阿拉爺,四九年已经去了香港开店,不过熬不牢香港的清苦,觉得乱糟糟,又回上海。之后想走也走不了,一直苦熬到文革结束,一口气併不牢,驾鹤西去了。
我大伯,旅居美国四十几年,想起上海,五味杂陈,午夜梦回,恍惚之间,勿晓得自家到底是在上海,还是外国。
在我小辰光,石库门,好几家人共用一个灶披间。老远就听到大人们讲,谁没有审批下来,谁出去了,谁来消息了……。
我一走过去,伊拉就一起不说话了。回到家里,我妈才说,怕我们小孩子家,嘴不严,把话传出去。
如果没有苦衷和不得不走的理由,有谁愿意远走海外,客居他乡呢?!
当然,在海外的上海人,很容易融入当地的,海派文化与生活方式使然,但心头对上海的不舍,也只能是“唧唧复唧唧”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不知泛起多少回。无论身在何处,这些海外的上海人心中始终怀揣着对故乡的思念和对上海文化的眷恋。他们在异国他乡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也尽可能保持着与家乡的联系。
这世界,很疯狂,也很真实。有的人,逃到上海,上海解放了。游到香港,香港回归了。到美国留学,好不容易拿到绿卡,发现机会其实没有国内好。这些不同时期的上海人,移民过程中的心声,不仅是个人命运的变迁,也是那个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见证者。他们的经历反映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以及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选择和牺牲。
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
作者:上海培训师周子淳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内容由用户自行上传,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处理,谢谢!联系QQ:2760375052